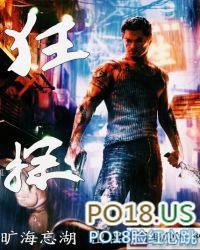小薇中文网>明家旧事/阿诚系列+巴黎风云 > 第16章(第1页)
第16章(第1页)
六月阳光如刺骨冰水将她从头到脚浸没,凝成门后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弟弟背脊挺直,沉沉地压在眼前,明镜怒不可遏,颤抖着质问他是不是忘了父亲临终的话。 明楼当即跪下否认。汪芙蕖是系里聘请的教授,著名的经济学者,即将上任的政府财政顾问,他兜兜转转解释了许多无关痛痒的理由,明镜却隐隐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。 你该不会是存了心思故意接近他吧,她问。 明楼抬起头,目光沉静,薄唇紧抿。 夏天,明楼南下去广州。上海的报纸铺天盖地都是广州国民政府成立的消息,新政府主席是汪兆铭,财政部高级顾问的名单上有汪芙蕖的名字。秋季开学,他又匆匆赶回南京。 半年过去,姐弟俩见面次数屈指可数,明楼联系家里也以问候为主,谁都没再提起那件事。直到明镜发现他给汪芙蕖写信,心里的刺又疼起来。 汪芙蕖是只笑面虎,和日本人关系匪浅,南边的政府里也有人坐镇,她怕明楼入虎穴有去无回,然而也知道他骨子里深藏执拗,凡是他决意要做的事情连父亲都未必能说动,她给再多巴掌也毫无用处。 明镜胸中亘了一口气,餐桌上只给明诚明台夹菜。狮子头肥腴柔嫩,汤清味鲜,明台从大姐碗里挖来半个,一人独占一个半,摇头摆尾吃得不亦乐乎。阿诚没什么胃口,剩了半只被明楼夹去吃了。撤下饭席,周妈妈端来红枣汤,嘀嘀咕咕说厨房里的耗子不怕猫,早间取的冰糖少了一半多。 明台闹着要看烟花,明楼在院子里点了几只窜天猴和金玉满堂,火树银花,热闹非凡。阿诚笑嘻嘻地倚着廊柱子看,他有些头重脚轻,也不吭声,晚上照常吃了药就去睡,没想到后半夜忽然发起高热来。 明楼睡得迷迷糊糊依稀听到梦呓,闭着眼睛往枕边摸,伸手触到阿诚滚烫的额头顿时惊醒。病情来势汹汹,找大夫来开药诊治是绝对不行的,他披衣起身找出电话簿。苏州城里有一间外国医生开的诊所,明楼找到诊所的电话,想起后院小楼只装了一部电话,在明镜和明台的睡房里。他不想吵醒姐姐,索性穿戴整齐,准备下楼去前院打电话,出门时恰好遇到明镜听到悉索声,推门出来查看。 从老宅到马路有一段距离,石板弄堂狭窄不能行车,轿车只能停靠在路口。明镜提着纸灯笼走在前面照路,阿诚已经是半大孩子,不便抱在怀里,明楼俯身背起他,双手稳稳地托在背后。 沿街一路灰墙高耸,星月无声,呼吸在寒夜里化作白雾迅速散去。阿诚有些醒了,动了动手脚,只觉得浑身的骨头疼得厉害,肺里呼出的热气能烫伤鼻腔喉管。他痛得委屈,忍不住呻吟出声,难受得要哭。 明楼侧过头,在他耳边轻声哄道:“别怕,我在。” 声音沉沉,似一道清流淌过,阿诚依恋这份清凉,贴在他颈侧含糊地念:“大哥”。 明楼搂住他往上轻轻一颠,仍是说:“我在。” 天上的星星被急促的脚步搅乱了,落在白纸灯笼里,透出温暖的微光。宽阔的背脊随着步伐摇晃,像温柔的海浪,轻轻推小船入了港湾。 风霜寒意都不见了,阿诚枕着宽广的肩膀,安心地睡过去了。 tbc苏州冬日(完) 时间:1926年,明镜29岁,明楼22岁,明诚13岁,明台8岁。 (五) 阿诚这一觉睡得极沉,醒来时恍惚不知今夕何夕。 他半梦半醒听到哔哔啵啵的动静,像是远处不断有鞭炮炸响,等他睁开眼,那声音变得更加清晰,似乎就在枕边。他望着墙上的耶稣像出了一会神,才反应过来这里是诊所病房。 窗边有一个人影,明台搂着铜火囱坐在窗前的椅子上,正低头透过盖子上的小孔瞧里头的动静。细碎的声响就是从这黄铜火笼里传出来的。他微微侧过头,半边脸陷在枕头里,带着刚睡醒时的迷茫和困顿静静地看着明台。 明台抬起头,正好和他的视线对上,立刻咧嘴笑起来:“阿诚哥,你醒啦。” 阿诚轻轻点了点头。嘴里干得发苦,舌苔黏着上颚,他下意识地朝床头柜上的茶壶看。明台跳下椅子给他倒了一杯水,学大姐的样子浅浅地尝了一口,感觉到水是温的才递过去。 如果大姐在,肯定会夸他像个大人了。明台有些得意。 铜火囱里渐渐热闹起来,捂在炭灰底下的米粒受热膨开,爆出轻微的声响。明台听声音知道白米差不多都开了花,搓搓手心旋开盖子,拿竹片拨开厚厚的灰烬,拣出一粒粒爆米花。满室温暖焦甜的白米香气像一团蓬松的棉花,阿诚陷在柔软的米香里深深吸气。 明台塞给他一把热乎乎的白米:“大姐说你两天没吃东西,一直在睡觉。” 米粒上沾了点炭灰,阿诚轻轻吹走灰尘,舌尖在手心里一转,舔走四五粒:“大哥大姐呢?” “大姐在和医生说话,大哥昨晚睡在这里,回去换洗衣服了。”明台眨了眨眼睛,忽然压低声音说,“大姐和大哥说话啦。” 阿诚有些糊涂,愣了一下才明白他的意思,心里的石头蓦然消失,微笑着说:“好呀。” 明台也嘻嘻地笑,拈了两粒香米花仰头扔进嘴里。椅子太高,他的脚尖碰不到地,两条腿悬在半空中晃呀晃,仿佛把那些藏在夜里的忧虑和烦恼都踢散了。 离开南京那天,大哥送他们到车站,一路叮嘱明台不要顽皮不要惹大姐生气,明台难得听话,回到上海安静了一段时日。那些日子里,明镜常常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出神。阿诚半夜起来,站在走廊上悄悄地往楼下看,灯光明亮一如往昔,大姐端坐在沙发一角,满室的寂静都落在了她的身上。那时,他才恍然发现明公馆璀璨华丽的水晶灯下也有光芒照不到的角落,大哥大姐温言笑语的背后是他和明台都无法触及的往事。 明镜进来时,明台已经脱了鞋和阿诚一道钻在被窝里,头碰头凑在一块焖蚕豆。豆子的熟香和白米的香气融在一起,软绒绒地搔着鼻腔。明镜惊喜地抱住阿诚,试探他额头热度,阿诚在豆香里又闻到了雪花膏的蜜香。医生和护士也进了病房,护士是学看护的本地姑娘,抿了嘴笑着看他们,阿诚觉得挺不好意思,毛茸茸的脑袋在明镜怀里转了转似要躲开。 医生是德国人,量过体温,用听诊器在阿诚前胸后背敲敲按按,让他反复深吸气再吐气,不发一言听诊完了终于露出一丝笑。他的英语带了刻板的德国口音,阿诚倒也听懂了,知道自己病好了随时可以出院,等医生一走就对大姐说要回家。他们正说着话,忽然听到窗玻璃上两记脆响,转头一看,是明楼。 病房在一楼,窗户外面是停车的空地。明楼下了车,习惯性往窗户里边瞅一眼,正看见阿诚醒了,倚在床上和明台明镜说话,他心里欢喜,几步走过去,抬手敲了两下窗户。阿诚眼睛一亮,笑着对他挥手。明台已经下了床,这时骨碌爬到椅子上,贴着窗玻璃喊大哥,哈出的雾气蒙上玻璃很快散去。仨兄弟隔着窗户嘻嘻哈哈地打招呼,明镜看到明楼两只耳朵冻得通红,心里疼惜,一叠声地催他进来。 明诚回家休养两天,渐渐恢复了精神,小年夜就着暖汤吃了几只蛋饺,胃口也眼见着转好,除夕这晚已经有兴致和明台在铜锅里抢冬笋和肉丸吃了。阿诚回家,最开心的人是明台。那天早晨他醒来不见大姐,隔壁房间里大哥和阿诚哥也不在,他不安地喊了几声没人应,以为家里出了变故,站在空无一人的楼上放声大哭。现在大家都回来了,日子又回到平常的样子,那些惶恐和惊疑就都遗忘在记忆的角落里了。 最后一道甜点八宝饭上了桌,雪白油亮的糯米饭上青梅丝红绿交叠,煞是好看。明镜顺口提了一句城里的戏班,明台突发奇想说要听戏。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,哪里还有戏园子开门迎客,但是明台在兴头上,劝也劝不住,非要听《淮河营》不可。明楼哄他高兴,唱了一段左拉李左车右拽栾布同爬鬼门关的西皮流水。明镜是爱听戏的,听他一个爬字拖腔带调,百转千回,不由得叩桌叫好。明台和明诚只会听热闹,见大姐这么高兴,也觉得大哥唱得极妙,卯足了劲儿鼓掌。 明楼在家时常哼上两三句戏词,多半是自个儿消遣,今晚来了兴致,一连唱了几段明镜爱听的《白蛇传》和《梅龙镇》,把她哄得喜笑颜开,自己也多喝了几杯。黄酒醺人,他似醉非醉,又唱了一段《借东风》。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,立功名兮慰平生, 慰平生兮吾将醉,吾将醉兮发狂吟! 同窗故友会群英,江东豪杰逞威风。 俺今督师破阿瞒,哪怕他百万雄兵! 据长江与敌争锋,显男儿立奇功。 调子起手悠长,忽而变得高亢激昂,字字铿锵,一曲终了,豪气尽数倾出。阿诚和明台拍手叫好,明镜脸上仍带着笑,却没有言语。明楼悄悄朝他们使了个眼色,两个小的得令,立即“红包”、“红包”地叫起来,明镜这才笑出了声,掏出早就准备好的压岁红包,一人一个塞进手里,悉心嘱咐用功读书,关照身体。 明楼也笑嘻嘻地凑过来,大大方方地向她伸手,明镜心里已经软了,嘴上还不肯轻饶:“多大的人了,还跟着讨红包。” 明楼的脸皮堪比城墙砖,歪理正理头头是道:“自古以来,长姐如母。大姐是长辈,是明家的天,在您面前,我也是小辈,过年自然要跟您讨份吉利。” 明镜知道他一张嘴,哪怕是古田枯木也能变出满树桃花,拿手指点一点他,嗔怪道:“虚头巴脑的,”一面掏出大红纸包放在他手里,轻轻拍了一拍,“你呀平平安安的,将来成家立业,做个学者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 明楼弯起嘴角笑了笑,说:“大姐放心,我明白。”他在宽慰人的时候常有这样的笑,温雅柔暖,能叫人心尖儿都舒坦。在明镜眼里,他还是长大了,脸上有了棱角轮廓,心里有了志向,这一笑背后的千言万语,做姐姐的也只看透一半。 这一夜,苏州城里爆竹声此起彼伏。他们聚在门前,爆竹放得最远,烟花摆得稍近一些,明楼让他们站在院门里边,自己拿了自来火去点捻子。烟花璀璨,阿诚和明台倚在明镜身边嬉笑不停,明镜搂着他们,恍然发觉他们都长高了许多,几乎到她的胸口了。总有一天,他们都会比她高出许多,和明楼一样,走到自己的前面去。她在漫天光彩中生出了时光催人的感慨,又暗笑自己大概是老了,竟然纠缠在这些心思里。 看明楼点了几支烟花,阿诚有些跃跃欲试,明台也心痒难耐,不住地拉明镜的袖子恳求。明镜笑着在他们背上拍了一下,说:“去吧,小心点。”小孩子们欢呼一声窜出去,挤在明楼身边争着点烟花。爆竹声响,消去旧年烦恼,她远远地看着他们围在一块,心里有无限的喜乐和安宁。 end =============== ps:小阿诚结束了,之后还会有少年阿诚。寒秋(一) 明家旧事系列。 1926年秋,明诚13岁,明台8岁,明楼22岁,明镜29岁。 (一) 阿诚哥。明台张了张嘴,声音散落在风里。 天上有一团模糊的白影,像一锅煮糊的汤圆。他仰着脖子望了一会儿,意识到那是月亮。 没有星星。浓厚的黑如山一般压在眼前,他小心翼翼地敛起视线,盯着脚下的路。 黑暗像是活物一般,亦步亦趋地尾随。参差不齐的屋脊是它的牙,冰凉的风是它的呼吸。它从屋檐底下露出大而圆的眼睛打量他们,悄无声息地贴近后背,往衣领里吹一口气。 明台一个激灵,伸手攥住明诚的衣角。 “别怕。”明诚低头看了看他,把他的手指握在手心里。 我不怕。明台想要反驳,话到嘴边顿了顿,没能说出口。怯意逮着犹豫,顺着背脊攀上来,蚕食微弱的热气,他缩起肩膀。夜里风凉,他身上只有一件单衣。 “阿诚哥,这是哪里?” 明诚朝四周望了一圈,周围什么都没有。他们脚下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,右手边有一条河,他看不清河面有多宽,只觉得草密水深。 苏州城里有很多河,他只认得几条。常去的餐馆后边的,青石栏水井边上的,祠堂前那条有着一排老柳树的,还有老宅门口静谧无声的小河。城里还有许多野河浜,不知从哪里冒出来,弯弯曲曲地流过田野,绕过石桥,载着舢板朝城外滑去。他记得大哥说过,苏州城里的河都是连着的。 “我们应该在南边。”明诚勉强辨了一个方位,其实心里也有点打鼓。 他们怕被人发现,从花园后门偷偷溜出来,沿着一道道狭长的巷子不知跑了多久,跑到尽头便是这条河,周围荒无人烟。 “南边是哪里啊?”明台耷拉着脑袋,无精打采。 “南边……就是南边。”明诚定了定神说,“再往前,就能看到人家了。” 他握着明台的手拽了一下,明台又抬起头来,加快了脚步。 风从河上涌来,像一头蛮横的小牛横冲直撞。对岸是庄稼地,黑黢黢的一片全是一人多高的玉米秧,风吹得玉米叶子簌簌响。明台时不时用眼角余光觑看河对岸,疑心那里会突然跳出个青面獠牙的怪物,张着血盆大口扑到他跟前来。 他被奇思怪想牵着走,不自觉地往明诚身上靠,一不留神脚下踩了个空,猛地冲出去。幸好明诚用力拉住了他才没有摔倒,但是毕竟是吓到了。 “阿诚哥,我们还要走多久呀?”明台的声音里添了微弱的哭腔。 明诚的心抽紧了。他们有过许多次冒险,在自家花园的假山上,在明堂哥家的泊船码头。这一次,若是被大姐知道他们在夜里冒冒失失地出门,多半是要挨骂的。 要不要回去?明诚犹豫了。已经走了那么多路,他不想就此放弃。 “你想回去吗?”他问明台。 明台吸了吸鼻子,没有说话。他也犹豫不决呢。 “如果你想回去,我们就回去。”明诚放慢了脚步,低头看他。 “不回去。”明台不情愿地摇了摇头。想要见大姐大哥的愿望压过了一切疲惫和惧意。他不愿意回家等,不知尽头的等待极其难熬,他就是等得受不了了才央求明诚带他出来的。 “那就再往前走。” “还要走多久啊?” “很快就到了。”明诚抬头看了看,前面隐约有一片突起的土坡,他拉一拉明台,指给他看,“过了那个坡就能看到了。” 能看到什么?明诚自己也不知道。他只是随口说了一句,给明台,也给自己鼓鼓劲。要是翻过土坡仍然什么都没有,怎么办? 他呼出一口气,摇了摇头,甩掉这个丧气的问题。 上坡的路有点陡。凹陷的路面上有很多马车车辙,错乱交织,越往上陷得越深,他们走两步就会被坚硬纵横的车辙绊到。然而谁也没有埋怨,只一味地奋力向前迈步。明台甩开他的手,几乎是手脚并用地往上爬。 河水在草丛深处静静流淌,他们喘着气爬上坡顶,不远处的河面上泊着几条渔船,船舱里漏出一星半点的烛光。 “看!”他们几乎同时朝那丝微光喊起来,一同放声大笑。笑声被一阵风卷去,盖过了野地里悉悉索索的动静。 明诚指了指前方黑影幢幢的屋舍,提起声音说:“沿着这条河走,就能到有人家的地方。” “嗯。”明台重重地点头,现在无论明诚说什么,他都深信不疑,“到了有人的地方,我们叫辆车去面粉厂吧。” “不行。”明诚摇头,“城门都关了,这会儿已经出不去了。”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影帝他从火葬场爬出来了 木头先生和花瓶小姐 禁止撒娇 凤霸天下 君王无情 [综漫]我成了港黑首领 星战英雄传 BOSS,幸运来袭 魔道祖师薛晓同人——星沉大海 BOSS主人,帮我充充电 [综漫]只好在番剧里做万人迷了 隋唐 太子万福 穿越之燕回 地球公测后我成bug了 锦绣女配:拐个反派来种田 极道美受 百态众生之商匪 娇妻入怀,顾少我超乖 [综漫]意外死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