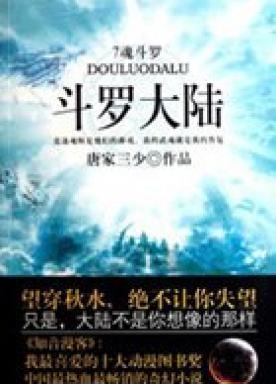小薇中文网>浪漫悖论TXT > 第41章(第1页)
第41章(第1页)
周遭嘈杂喧闹,几个人欢呼地击掌,什么东西突兀地炸开,然后有漫天飘洒的白絮落下来。她的思绪跳跃,望远处三个人挥洒着手里喷罐的模糊身影。栽在女人颈间,微微平复呼吸。然后又伸出手去,抓住那些湿漉漉的白絮,语序颠倒地说,“好像雪啊,好看。”“你不是最讨厌冬天吗?”喷洒的气罐声中,女人的声音也有些模糊,又或者是因为被她咬重了,这时候说话还有些含糊。“是啊。”付汀梨迟缓地说,“可是,我还是挺喜欢雪的。”“小时候去过一次北疆,那里很冷,雪也很多。”“北疆哪儿?”“喀纳斯那块。”女人没说话了,只轻轻抚摸着她的发。停顿一会,才说,“我没去过,好看吗?”“那太可惜了,那里的雪和其他地方都不一样,特好看。”一来一去的对话戛然而止,没人再接着往下说,也没人再往下问。纵使付汀梨这时候有些酒劲,这时候也问不出那句“要去看看吗?”或者再在这句话里,加上“一起”两个字。这不符合旅途规则。“什么北疆!”而这时候,祝木子却跑过来,拿着喷雪罐往她们周围喷,兴冲冲地问,“你们要去北疆看雪吗!”付汀梨听到这话,晃了晃脑袋,挣扎着从女人颈间抬起头,“没有,就是提起那里的雪好看而已。”“我们不去。”她强调,却不知道这句话是说给谁听。周围白絮铺天盖地地往下落,又被风吹着,缓缓飘在她们周围。付汀梨晕头转向地伸手去抓,抓到了就眉开眼笑,没抓到也弯着笑。祝木子叹一口气,“好吧,我还以为你们也去呢。”“你们要去?”回应她这句话的,是之前从来没和她说过话的女人。“打算去。”祝木子搭着另外两个人,大大咧咧地说,“还想着你们要是去我们可以顺路一起。”“不过也没关系。相逢即是缘,只要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,我就开心了。”这人年纪轻轻,说话却老派。付汀梨听了一句,在心里偷偷地想,而且她们可不算什么有情人。结果后退的时候一脚踩空,东倒西歪地往后倒,却被一双手稳稳捞住。带了回去,又栽倒在熟悉的柔软处。她眯了一下眼,觉得这世界实在天旋地转,像个万花筒似的在面前转悠着,索性就安然地窝着,再不出去胡作非为。女人拿起付汀梨刚刚喝了一半的酒,和祝木子轻轻碰了一下,而后又说了几句付汀梨听不清的话。在嘈杂喧闹的声响里,付汀梨睁开眼,恍惚地望飘散的白色雪絮。冷不丁被呛得咳嗽,连着咳嗽几下,嘴里的血腥气和酒精同时在弥漫。她想起刚刚咬女人时的力道,心想血都散到她嘴里了。这个女人怎么还若无其事的。甚至还能大口灌酒沁进伤口,这人是真不怕痛,好像也不怕死。而下一秒,她看到女人下巴微抬,又灌了一大口酒进去,一点一点把那些为非作歹的酒精吞下去。然后似是没忍住痛意,不露痕迹地皱了皱眉。付汀梨伸出手指,抚了抚女人的唇,语气肯定,“你是故意惹我咬你的。”女人头发飘在远处灯火里,微微垂眼,朝她不痛不痒地笑,“那你会记住吗?”付汀梨后来才知道,酒精并非她的特异功能,她没办法仅仅靠靠酒精去印刻一段记忆。因为那时她已经记不得,自己当时是怎么回答的的,好像是说“不一定”,因为她并不是被咬的那一个,不怎么痛;又好像是说“可能吧”。她只记得,在她的回答之后发生了一件事。是aanda喝高了,突然冲到她们身后的车上站着,面对着呼啸而过的轻轨列车,特别努力地用中文,大声喊了一句,“祝木子!”呼喊声被灌进风里,都已经快要听不见,可aanda还是微微曲腰,竭尽全力地将那句话喊完,“我爱你!”于是她和女人同时抬头去望。她还头晕着,仰头的动作有些费力。只看到本来在她们旁边靠着的祝木子,立马冲到车上去。扑进aanda怀里,然后喘着气。又对着那快走到末尾的轻轨,对着那一大片穿梭的亮光,对着亮光里的陌生人,大声呼喊,“祝曼达!祝木子也爱你!”付汀梨愣愣望着,鬼使神差地去望自己旁边的女人。又恍惚着去望那一对在弋风里抱得很紧很紧的人。她们的头发被吹得好乱好乱,她们的身上好亮,像是在发光似的。脑子里冒出无数个飘渺鲜活的爱情故事,瞬间有什么东西在心底横冲直撞,像一把疯魔的枪,劈天盖地,一击即中,击穿她过往的所有认知。她从未体会过那样浓烈的爱。当下只是稀里糊涂地说,“原来这就是有情人啊。”而女人也在风里望她一眼,然后去望祝木子她们,然后又照顾着也跟着抬头也笑得畅快的nile。好像没说什么。却又好像在付汀梨快要睡过去之时,轻轻按了按她的后脑勺。她还记得,那时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,人造雪絮缓缓下落,头顶轻轨呼啸而过,只留下一阵余韵难消的尾音。她又没忍住咳嗽一声,似又有不属于她的血腥气溢上来。而女人轻轻地说,“那就祝有情人,终成眷属吧。”后来再回上海,付汀梨总在飘摇的雪里,一次又一次地咳嗽,五脏六腑都跟着痛,像一次迟来的答复:不是会记住,而是到死也忘不掉。「爱与悖论」火车声来势汹汹,撕扯变幻莫测的时间隧道,飞驰而过,将空荡公路瞬间颠倒为密闭走廊。付汀梨仰靠在墙边,伸直的腿上搭着孔黎鸢的腿。孔黎鸢攥着她的手腕,指腹抵住她右手无名指指关节上的疤。她用她看不懂的眼神望住她。光线晦暗,付汀梨莫名咳嗽一声,再抬眼,透过孔黎鸢直盯着她的眼,看到衣帽间镜子里的自己。面色苍白,眼睫没有气力地耷拉着,黑发散乱挤在颈下,一副破败落魄的景象,没有任何过往可言。以至于她有些恍惚,在孔黎鸢刚刚问出那个问题之后反复回想:在加州的时候爱不爱?再次回想起加州,她只觉得那句“有情人终成眷属”太过理想化,不太适合这平庸忙碌、存着身份差距的世俗。更何况,她和孔黎鸢,又什么时候算有情人了?只不过才三天三夜的时间,就算她回过头来说那个时候她好像真的是爱,都不是那么合适。可她依稀记得,那次加利福尼亚的夏天,好像只有三天。那时的她,和孔黎鸢看过加利福尼亚三十六度的日落,你一口我一口地吃过同一个汉堡。在敞开的那辆白色老车里,她一伸手就能碰到她的发,一个眼神她们就会不要命地接吻。但让她铭记于心的,绝对不是加利福尼亚的夏天。这算爱吗?她记得,第一次说“我爱你”,是在乔丽潘和付问根离婚之后,她牵着乔丽潘的手,摸了摸上面的茧子,有些费力地仰头,对乔丽潘说“我爱你妈妈”。她不知道,为什么只是这样一句话,就让一向强势的乔丽潘一下红了眼眶,抱着小小的她蹲在马路上嚎啕大哭,像个疯子似的。但她想,如果妈妈是疯子,那她大不了也当个小疯子,她永远和妈妈站在一边。后来她走丢,乔丽潘在冰天雪地里找到她,热切又暖烘烘地抱着她,流着滚烫的眼泪说“宝贝妈妈爱你”;再后来一段时间,乔丽潘会在她每天出门前亲她一口,她懵懂地摸摸湿漉漉的额头,乔丽潘会把她抱得紧紧的说“妈妈爱你”;甚至再后来,因为她一过冬天就全身难受,感冒发烧变成常态,于是乔丽潘狠心,将所有业务都移到没有寒冷冬天的加州;最后,乔丽潘破产负债,一声不吭地将她送回国,给她留好退路……付汀梨逐渐在这些事情中明白一个道理我爱你,一直就是那么好那么纯粹的一件事。再次回想加州那三天,她觉得那是好的,是纯粹的,她们牵手逃亡接过无数个轰轰烈烈的吻,不问姓名不通身份,在陌生国度横冲直撞地度过三天。那是最好最纯粹的三天。可回到上海,她们被鲜明地划分在两个世界,再来谈她在那个时候爱不爱她,就有些不切实际,连那三天都不能算数了。四年前的付汀梨当然可以说爱就爱,也可以自信、毫不吝啬地爱上一个在公路上偶遇的女人。但对现在的付汀梨而言,爱不爱,要不要爱,愿不愿意爱……都已经不是她做事的首要标准。她被困于杂乱出租屋的三十瓦灯泡下,被困于要命的自尊感中。只知道世间万物都有期限。她不再轰轰烈烈、不再崇尚新鲜感、不再义无反顾去追逐故事的过程而不问结局。就连爱,也变成了最没有价值的东西。但好像无论如何,二十四岁的付汀梨都没办法杀死二十岁的付汀梨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大唐女法医 不可语怪力乱神 奶妈在全息游戏捡破烂 大师兄逃难记 医心方 机器人幼崽进娃综成团宠 动物情书[娱乐圈] 撩人的手,微微颤抖 我靠病娇的吻续命[穿书] 我竟不知老年生活如此快乐 猫巷 清穿之卷王十四爷 约定在星期天晚上 桃花中学 强行成为灭世反派的师兄后 冤种师兄让师尊火葬场了 白月光是小奸细 向天借了五百年 信不信由我 钟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