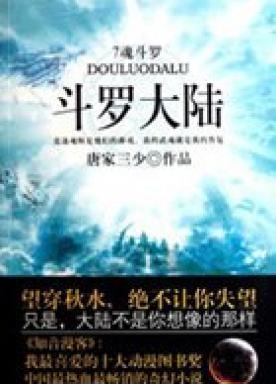小薇中文网>佛兰德之冬 > 第3章(第1页)
第3章(第1页)
‐‐就像我们。
‐‐是的,就像我们。基于这个相似之处,这个故事才值得一讲。
第2章乞援人
我不知道故事应当怎样开头。或许不从画家的时代说起,而是从他死后一百年说起。现在的时间是16世纪后半叶,我们星球的一个奇异的新模样正初现端倪。或者说,它在人们心中的样子正在瓦解。如果要我打个比方,它曾像佛兰德古画里上帝握在手中的玻璃球,沉静剔透,之中包含了世间万物。这个完美密闭的玻璃球正在分崩离析,身处其间的人们却并不能即刻察觉。航船驶向未知之地,人们知道了海那边有坚实的大陆,上面生活的虽不是古书里描绘的怪物,但要说他们是和自己一样的人,人们也会大惊失色。现在再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旧大陆,何等眼花缭乱的景象,在地下发掘出了古代的大理石像,甚至是一整座城,在旧书堆里发掘出了沉睡已久的语言和诗篇,在人人熟悉又陌生的新约里发现了新信仰,在夜空里发现了星辰的新规律,在身体里探查出了血液的流向;但人们不会因此更加睿智,也不会因此流血流得更少些。此时离比利时诞生为时尚早,低地诸国正在西班牙手中。也许只需说,我们脚下的土地与其上的人们一直羁绊甚少。我们的佛兰德就像一片孤零零的叶子,早已忘记了主宰自己的滋味,或者相反,它对自己的主人并不在意,只是悬挂在那里,任由自己在空气中飘荡。它的主人姓甚名谁,并不能改变这条或那条河道的流向,也不能阻止这头或那头牛犊被割开喉咙。
现在看看谁来了,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,他用厚重的毡袍抵御严寒,艰难的步伐与其说是被风雪所阻,不如说是被什么畏惧或痛苦所阻。天太冷了,需要烧柴火,可是森林属于老爷们,属于尊贵的国王,野兔在被撕裂前尚且可以享用神圣的森林,人却不行。可从远近的烟囱里升起的这些白烟来自哪里呢,这气味是最优质的椴木,还带着彩漆和焚香的味道。烧红的炉膛里迸起的残烬,曾经是圣安东尼的头颅,是圣卡特琳浓密的长发,是三王来朝的画板。英勇的圣像破坏者们洗劫了佛兰德的教堂,我们尽管让议事司铎们去痛哭流涕,让英雄们先欢呼后躲藏,这是他们应得的。这些抛在街角的木头终于被当成了木头,缺粮少柴的居民们不偏不倚地对待了它们。现在,不是我们为圣母玛利亚披上金衣服,而是圣母玛利亚为我们噼啪燃烧。现在圣像没有了,但它们终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温暖。今天晚上怎么这样暖和呀,瞎眼的老祖母会这样说,然后安详睡去。整个城市的天空都弥漫着焚烧圣像的味道,圣徒们交融在一起,从未如此亲密无间地充盈了我们的肺腑,通过血液与我们同在。这是真正的诸圣相通,向轻烟祈祷吧。
这是沿着大桥走过去的赶路人心里的想法,我们姑且认为他是这样想的,对于当时的缕缕轻烟如何飘向阴沉的天空,他看得比我们更清楚。现在钟声敲响了,没有人会拒绝钟声的。圣巴夫,赶路人望向钟塔,头一次在所有的名字中呼唤其中一个,圣巴夫,愿钟声保佑你和你的钟塔,愿钟声保佑你和你的教堂,愿钟声保佑你和你的根特。人们把这一小块土地上矗立着的一切交在你手中,垒起的石块,柱子和柱廊,拱券和长窗,祭坛和烛台,你不愿意要它们,你厌倦了保护它们。你没有发现你的大教堂里少了什么吗?谁知道紧锁的钟塔上面有什么:亚当和夏娃都沉默着,圣人和义人们都沉默着,天使们蹙着眉头,张着口,也不发一言,或许他们从没停止过歌唱,只是我们听不到这歌声。神秘的羔羊沉默着,就像被巨鲸吞噬的约拿的沉默。钟塔纵横交错的木梁就像鲸鱼的骨架,他们都呆在它的肚子里,听着钟声作响,就像鲸的心跳。原谅我们这些凡人的虚妄,我们太自私了,不愿意让扬和于伯特兄弟的祭坛画变成劈柴。谁又知道佛兰德有多少钟塔,多少地窖,藏着多少只神秘的羔羊,愿它们像世上所有的羔羊一样沉默。
骑在马上的军官也听见了无所不在的钟声,闻到了无所不在的轻烟。他用裹着黑皮手套的手在胸前画了个十字。这是个西班牙人,称呼他得用&ldo;堂&rdo;打头,就像报幕人的开场词,就像一声洪亮的号角。我们随便叫他堂˙佩德罗,堂˙罗德里戈,堂˙伊西多罗,或许叫堂˙迪亚戈更好,这是西班牙人对雅各的叫法,是对银河的叫法,是对大路的叫法,人们就是循着这些大路,从欧洲每个角落来到西班牙朝拜圣雅各,传说耶稣派他给西班牙带去福音。雅各就是道路的别称,是地上的道路和天上的道路,从今往后还包括海上的道路。堂˙迪亚戈戴着尖拱型的头盔,闪闪发亮,就像迎风破浪的船头。佛兰德人见到这样的装扮,无不咬牙切齿,心惊胆战。
堂˙迪亚戈跟随臭名昭著的阿尔瓦公爵的军队,是其私费尔南多的得力将领。他家有悠久的军旅传统,从摩尔人手中拿下格拉纳达时,他祖父就在天主教女王的军队里当步兵上尉。他从小就听着祖父一遍遍讲着山上摩尔人宫殿的奇景,说当他们迈入荒废的庭院时,只有燕子统治着那片蜂巢似的迷宫。谁相信这半盲的老头也曾喝过异教徒的泉水,也曾爬得和燕子一样高,现在他连家门口的鸡仔也逮不住一只。堂˙迪亚戈年轻气盛时,曾跟几个相熟的船商之子参加远征新大陆的舰队,盘算着给自己冠上征服者堂˙迪亚戈的名号。他们的大船抵达新西班牙岛时,他一度相信,围绕自己的海鸟比整个格拉纳达上空的燕子加起来还要多。1541年,他卷入两位征服者皮泽洛和阿尔马格罗的争斗,前者被后者的帮派乱刀刺死,堂˙迪亚戈则伤及大腿,高烧不退,差点儿死在新托莱多。大病初愈时,不知是由于厌倦了赤裸裸的争地,还是由于家里殷殷恳求的急信,他再度横跨大海,回到了旧托莱多。此后几年,他蛰居不出,整日翻腾旧文书,甚至试图写回忆录。坊间传闻他与摩尔商人交往甚密,都笑话他在新大陆呆久了,只愿与野蛮人与异教徒为伍。1547年,堂˙迪亚戈返回战场,在米尔贝格战役里表现勇猛,得到了阿尔瓦公爵的青睐。他大部分的军旅生涯在地中海的战船上度过,沿着柏柏尔海岸线与海盗交手,一次次试图争夺丹吉尔和阿尔及尔。前往佛兰德镇压叛乱,或许并非堂˙迪亚戈的本愿。说起佛兰德,他只在威尼斯一间小教堂见过那里来的圣像画,在习以为常的海风的炎热中,他头一次感到难以言喻的冷意。现在,这种冷意终于蔓延到了空气里,如影随形地跟着他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白刃上蔷薇 尸雾小镇 当本尊的心上人跳崖后 旅行琴蛙 哥儿在末世[古穿末] 我成了全星际娇宠小幼崽 我的漂亮男孩 短篇 邂逅 心跳的距离 被搁浅的遗憾 女瓣:违纪的战争 穿书之浮梦三生 婚令如山:司少智擒小萌妻 沙雕经纪人,军训爆红 回忆里的,金色阳光 攻略失败后我摆烂了 深海里的舟 公主病观察日记 从零开始当国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