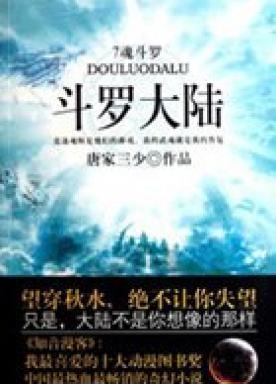小薇中文网>太阳雨太阳能热水器 > 第64章(第1页)
第64章(第1页)
“当然。之前,我们一直在一起。” 时没忍住笑了:“你所谓的在一起,就是我用手段绑着你,你不情不愿地履行合同?” “不是。” 傅宣燎想说不是的,起初因为误会不情愿,后来又因为害怕沦陷才竭力抗拒,我们的纠缠是双向的,爱也是双向,怎么能用一纸合同掩盖一场两情相悦? 可是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,晚到提起“爱”这个字,换来的只有冷笑和讽刺。 来不及,回不去,做什么都无法挽回。事到如今,傅宣燎才真正体会到被推上绝境的滋味。 他深吸一口气,拿出从时怀亦那里弄来的合同原件,摆在时面前。 “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,未经任何一方的允许,不得随意终止。” 傅宣燎将注意事项其中的一条念给时听,然后作为其中一方表态,“我不同意,所以合同继续履行。” 时这才知道,他消失几天,把自己弄得筋疲力竭,竟是为了这个东西。 一种难以言喻的荒唐漫上心头,像是走进一座巨大的迷宫,四周都是路,却不知哪条通往出口。 时不允许自己往后退,负隅顽抗般的低着头:“我不要,你走。” 没坚持多久,就被傅宣燎轻轻捏着下巴抬起视线,去看他手中另一件东西。 一张纸,展开是一幅画,线条粗劣,色彩搭配亦算不上纯熟,风格却很鲜明。若是那幅《焰》还在,和这幅放在一起,说不定会被认为出自同一人之手,或是有心模仿复刻。 哪怕画的主体并不相同,那幅画的是火,这幅画的是雨。瓢泼的雨浇灭燎原野火,本该是一场本能的主权争夺,那看似强势的火却主动敛去声息,由着雨将它扑灭,将它包围,心甘情愿的,毫无怨言的。 如果说《焰》是渴望,那么眼前这幅,诉说的便是臣服。 时本不想解读这幅画的内容,可傅宣燎太过粗暴直接,在用所有行动诠释他立下的承诺。 “你不是说,只要能原样恢复,就可以吗?”傅宣燎说,“你给我的没办法复原,但我给你的,掌控权在我手里。” 言下之意便是现在,我把我的心交给你。 而爱与恨,本质是一场零和博弈,一方的进攻和胜利,必然造成另一方败退与损失。 听到心里传来的类似零件松垮的声音,时抽走傅宣燎手中的画,拿起窗台边的打火机,拇指转动砂轮,让火焰吞噬那张薄薄的纸,以最快的速度将它烧毁。 一切发生得太快,色彩绚丽的画瞬间化作一摊灰烬,傅宣燎望着眼前的景象,张了张嘴巴,似乎呆住了。 时却松了口气。 历史重演就算威力不再,就算无法让时感受到快意,也至少会给一点逃出生天般的轻松。 “我不需要补偿,我什么都不要。”捻了捻指尖的一撮余灰,时宣布道,“已经没有了,你可以走了。” 他以为这样总该够了,没理由再继续强词夺理,孰料下一秒,傅宣燎突然大步上前,扯过时的胳膊,一使劲,将他按在墙壁上。 还没反应过来,灼热的气息伴着铺天盖地的吻,落在时的脸颊、唇角,还有不知何时变得通红的耳廓旁。 每逢此刻,势均力敌的关系总会变成单方面压制。傅宣燎一面压着时柔软的唇,一面毫不费力地用一只手将他两个手腕制住,图方便地压在头顶,再倾身过去,将这个吻不断加深。 他们太久没有亲密接触,以致忽然间的皮肤相触都堪比电闪雷鸣,能量巨大到霎时唤醒许多个夜晚身体交融、不知餍足的记忆。 暌违已久又过分熟悉的唇齿纠缠绵长而彻底,像急于把缺失的那些日子一次性补回来,所有感官为贪婪让路,两个人惯性地闭上眼睛。 犹如置身沼泽,越是挣扎就越是被缠得更紧,时绷着神经在紧握混沌中微薄的一线清醒,才找到机会张开牙齿,狠狠咬下去。 血腥味蔓延的瞬间,随着一声吃痛的倒抽气,身体的压制转换为眼神的禁锢,傅宣燎微微弓着背,自上而下地看着刚咬他一口的人,呼哧呼哧喘着不知是兴奋还是愤怒的粗气。 不,没有愤怒。 时看见那双他描绘了许多次的深邃眼睛里,除了稠密的怀念,唯有泛滥的痴迷。 好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,压抑许久的天性终于迎来释放,他嘶吼着、近乎狂热地在自由的天地里撒欢奔跑。 “我不走。”傅宣燎的眼神和呼吸同样炽热,“我知道,你不想我走。” 如果说之前的判断都是推测所得,这次便是经由过往实践得出的肯定。 面对他的逼近,时大可像之前那样无动于衷,冷漠抗拒,可时选择了抢夺和销毁,正是仍然在意的证明。 总算在这场难熬的拉扯中获得正向反馈,傅宣燎迫不及待地扯松左边衣领,拽到胸口处,让时看皮肤表面印刻的痕迹。 还是那场雨。 时慢慢睁大眼睛,看着刚被销毁的那幅画活了过来,落在一个连着心跳、渗进血肉肌理、只要活着就不可能磨灭的位置。 嘴唇翕张,半晌,时颤声道:“你疯了……” 见他终于给予反应,傅宣燎呼出一口气。 “是啊,我疯了,以前是你疯,现在换我。”傅宣燎扬唇,“你看,我们是不是绝配?” 先是你偏执地强求我一场,再是我偏执地非要把你抢回来,这才叫公平。 他松开时的手腕,握住其中一只手,让柔软的掌心准确抵在自己起伏的胸膛。 “我把恢复完整的一颗心交给你。现在,轮到你兑现承诺了。” 时从身到心都在发着抖,触着灼热皮肤的掌心尤甚。 他想不明白,明明表达了抗拒,甚至为了佐证态度说尽难听的话,做尽过分的事,眼前这个人为什么还是可以坚持如斯,不屈不挠地黏上来? 难道他知道了? 这个想法刚冒头,就被时摁了回去。 不,不可能,他不可能知道,他甚至都没有走进来过。 喧嚣的心跳暂且被安抚,时垂眼咬唇,用舌尖舔去不属于自己的味道,却意外地让铁锈味在口腔弥漫。 他这一口力道十足,直将傅宣燎嘴角都咬裂。鲜红的血顺着嘴角向下淌,被傅宣燎用手背揩去,另一只手还抓着时的手腕不放,高大身躯笼罩在上方,是一种听不到回答就不放人走的架势。 最后的底牌亮出,他的心也在狂跳,期待与害怕并行,如同等待审判的罪人。 可是时却说:“你不用这样。” “不用做这些。” 不用变成疯子。 “你本来就没做错什么,所以不需要求得原谅。” 我本来就不该把恨倾倒在你身上。 傅宣燎的心悬了起来:“那你,不再……” 甫一出口,他就意识到不能这样假设,这样约等于给对方提供破局的方法。 果然,时顺着他的话,替他补全未尽之言:“是的,我不爱你了,也不恨你。” 傅宣燎忽地怔住。 他没想到,从未将爱宣之于口的时,先说出口的却是不爱。 不再爱,也不再恨,一切都成了比过往云烟还要虚渺的空荡。 抬起头时,时眼底的迷惘失措已然褪去,取而代之的是比先前更加理智的沉静。 “对于过去的所作所为,我也该对你说声对不起。” 对不起,像个疯子一样缠着你。 “不,你没有……” 眼看傅宣燎着急反驳,时一改疏于开口懒得多言的习性,抢先一步将主动权握回手中。 “我没有承诺能给你。”他终于回答了那个问题,“也不想要你给我的任何东西。” 一场来势汹汹的危机化解于无形。 许是受了打击,之后几日,傅宣燎没再步步紧逼,却也不曾愤然离去,偶尔时出门采购生活用品,或者去医院复诊,还是能在不经意的回头时看到他的身影。 安静得连潘佳伟都不适应,有一次问时:“那个大哥……就是从事特殊职业的那位,是回去工作了吗?” 时这才知道他俩之间还有过关于背景来历的交流。 答不上来,时说:“不知道。” “唉。”潘家伟叹气,“看他那么生猛,还以为能多坚持一会儿呢。” 言语中大有棋逢对手、英雄惜英雄的意思,分明前两天刚经历完“生死时速”的时候还骂骂咧咧,说傅宣燎简直不是正常人,亏他还帮他说过话。 过了会儿,时问:“他告诉你的?” 指的是职业这件事。 潘家伟想了想:“也不算吧,是我猜的,他没反驳,你之前不是说你和他以前是……那种关系?” “嗯。”时低头看一眼掌心。 人们都爱用有名无实来形容貌合神离的契约关系,他和傅宣燎也是契约,却是有实无名。 不过本来就是一段从皮肉交易开始、难以启齿的纠葛,所以怎样定义都可以。 过完生日,一年也差不多走到尾声。 通过这些日子的复健,时的右手已经恢复到可以正常用筷子的程度。 先前因为不方便,江雪给他买了双儿童用的训练筷,两根连在一起,手指可以套进去,顶端还镶了小动物玩偶的款式。 时不觉得哪里丢人,用了好久,现在已经可以用这筷子顺利夹起花生米。 这天,他试着把一整盘新炒的花生米从一个盘子夹到另一个盘子里,只花了不到五分钟,并且手部关节仅有些微酸痛,他忙坐到画板前,久违地用右手画了幅速写,模特就是那盘花生米。 画完拍照发给江雪和马老师,江雪直呼明天就开始给他准备复出的画展,马老师也很欣慰,说:“照这个恢复速度,说不定能赶上决赛。” 时用左手绘制的那幅人像画,已经高分通过初赛预选。不过他没有乐观到认为自己左手的画技已经炉火纯青,能得到评审青睐,多半是因为题材恰当。 想起那幅画上的主角,时犹豫一阵,到底还是遵从内心,将这幅代表他有所恢复的画仔细地卷起叠好,放在垫满泡沫纸的箱子里,寄往经常给他寄来东西的那个地址。 响应速度超乎想象的快,寄出去的第三天,时就收到回信。 李碧菡在信中说:从小到大你都是个坚强又果断的孩子,无论别人说什么,都可以坚持自己的热爱。为你高兴的同时,我亦感到惭愧,为之前二十多年的得过且过,如果我早些下定决心,现在就不用在这里为身外之物奔走忙碌,实在自找麻烦。 随着来信增多,李碧菡写信的语气也越发熟稔,起初还有些拘谨,如今似乎已经把时当成相识多年的老朋友,无论是掏心窝子的还是家长里短,什么都说。 见她把离婚官司形容为自找麻烦,时抿唇一笑,心里自是知道她努力维持和时怀亦的婚姻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孩子。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帝业如画 影帝让我乖乖睡觉[穿书] (火影同人)说好的灭绝人类呢? 我家小猫咪超凶![穿书] (香蜜同人)如梦令 仙侠女主被攻略日常 跟踪情敌被发现后 你比可爱多一点 重生后主角反派对我情根深种 (综港剧同人)综港之三女成墟 他们闪婚啦 红糖鸡蛋 吃货世子俏厨娘 宫斗大佬群带我C位出道 重生之子承父业/重生之子承父液 不坠青云 禄星 娱乐圈生存法则 还珠之帝心欢瑜 明月漫千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