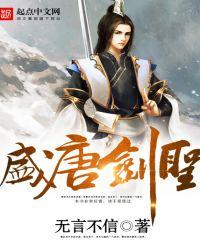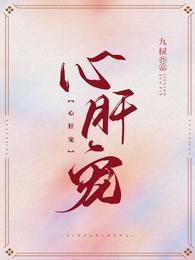小薇中文网>闲话中国人pdf > 第9章(第1页)
第9章(第1页)
这位头戴羊角身披羊皮的巫师或祭司,是在人神之间进行种种交易的&ldo;经纪人&rdo;。他的任务之一,便是&ldo;代神立言&rdo;。神祗之言当然都是吉祥的,或被希望为吉祥的。吉言也就是&ldo;羊言&rdo;,即&ldo;善&rdo;(善言)。善的字形,原本是上面一个&ldo;羊&rdo;,下面两个&ldo;言&rdo;字。许慎说:&ldo;善,吉也。从言,从羊。此与羲、美同意。&rdo;当然和羲、美同意的。因为它原本就是&ldo;羊人&rdo;所说之&ldo;吉言&rdo;啊!
于是,羊,不起眼的羊,默默奉献的羊,被捕捉宰割的羊,被&ldo;食其肉、寝其皮&rdo;的羊,就这样地既被人推上了祭坛,又被人推上了神坛。
有奶便是娘
这一点都不神圣,但事实就是这样:在远古时代,伟大的神圣的,往往就是可吃的和被吃的。因为被吃,所以理应受到回报(祭祀)。同理,但凡被请来吃的,神也好,人也好,也往往同时要&ldo;被吃&rdo;,‐‐或者曾经吃过,或者预备要吃。曾经吃过就现在回报,预备要吃就提前回报,反正从来就没有白吃的,也不能白吃。如果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受人一食,则很可能还要报之以生命。
比如韩信。
韩信是一个挨过饿的人。韩信少时家贫,常常到南昌亭长家去混饭。亭长的老婆显然并不欢迎他,便一大清早就把饭提前做好,在床上就吃光了。韩信再来时,当然没有吃的,一怒之下,便跑到河边去钓鱼。一个在河边拍絮的大娘(漂母)见他饥饿,便把自己的饭分给他吃,天天如此,直到漂絮工作结束。所以后来韩信封了楚王,衣锦还乡时,第一件事就是去报答那位漂母。
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,韩信在楚汉之争的最后关头便不肯背叛刘邦。因为他念念不忘刘邦&ldo;解衣衣我,推食食我&rdo;之恩。韩信说:&ldo;吾闻之,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,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,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,吾岂可向利背义乎!&rdo;所谓&ldo;死人之事&rdo;,就是&ldo;以必死的精神为他人办事&rdo;,&ldo;为他人之事不惜献出生命&rdo;的意思。一饭之恩,竟大如此。
其实,不仅韩信,只要是稍微感受过一点饥饿之苦的人,都会产生相同的感情。的确,挨过饿的人都知道食品的宝贵,死亡的危险往往是最好的教员。因此,在我们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,便积淀着这样一个观念:食物是生命之源。提供食物,即赋予生命。
母亲,就是这样一个生命的赋予者。
几乎所有人一生下来,就是母亲给吃的,先是吃奶,后是吃饭。这个过程往往要延续很长一段时间,直到那孩子长大成人。因此,在一般人心目中,母亲最亲,同时也最伟大、最神圣、最值得崇敬和感激。实际上,娘亲娘亲,不亲在生,而亲在养。一个呱呱落地的婴儿,哪里可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?也不会有什么&ldo;血缘&rdo;之类的观念。那他怎么认识妈妈的呢?还不是吃奶时认下的。如果他的生母并不喂奶,就很可能和奶妈更亲。甚至&ldo;贵为天子&rdo;(如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),也如此。中国民间许多地方都把母亲的中国叫做&ldo;妈妈&rdo;,把吃奶叫做&ldo;吃妈妈&rdo;。这就等于说,母亲就是辱汁,就是哺育者。所以,但凡对我们有哺育之恩的,也就同时具有母亲的性质,可以也应该被看作母亲,如辱母、养母。再广义一点,如母校、母亲河。总之,有奶便是娘。
有奶便是娘,这话似乎不中听,却很实在。因为给我们吃的,就是给我们生命。这又显然是只有神才做得到的事。所以母亲就是天,就是神。事实上世界各民族最早创造出来的神,差不多都是母亲神。欧洲是这样,中国也是这样。这些母亲神的偶像都有着隆起的肚皮(意味生育)和硕大的中国(意味哺育)。红山文化遗址甚至还出土了一大批中国。这么多这么大的中国,当然不是为了表示性感,而是为了吃。或者说,为了生存,为了获得和维持生命。这是不能不感恩戴德的。谁要是不感激,那就是没良心。不但要受谴责,而且要遭报应,也许再也没有吃的。
于是,中国们和有着硕大的中国的女人们,就这样走上了神坛。这里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观念:被吃的也应该是被感激和被崇拜的,可吃的也必然是伟大的和神圣的。反过来也一样,伟大神圣的,也一定是可吃的。国家是伟大神圣的(同时又是我们的母亲),所以是可&ldo;吃&rdo;(吃皇粮)的,而且吃起来丝毫用不着&ldo;不好意思&rdo;。上帝和神也是伟大神圣的,所以也是可&ldo;吃&rdo;的。古埃及人吃神王奥西利斯身上长出的麦芽,基督徒则吃象征着耶稣血肉的葡萄酒和面饼。这一圣餐仪式表达的大概正是这样一个观念:只有那些给了我们食物的,才真正是我们的上帝,我们的主。或者说,谁给我们吃的,我们就把谁看作天、看作神、看作上帝。
但这还不是母亲的全部文化意义。
正文第一章饮食二生命与血缘2
吃出来的血缘
母亲是个体生命的赋予者,也是血缘关系的缔造者。
中国人是很看重血缘关系的。在中国人看来,只有血缘,才最亲密、最稳定和最靠得住。谁都知道&ldo;是亲三分向&rdo;,血总是要浓于水,自家人也总是比外人可靠。这样,中国人在和别人打交道时,就总是要千方百计把非血缘关系变成血缘关系。拜把子啦,认干亲啦,要不就是把明明不是血缘关系的说成是血缘关系,比如父母官、子弟兵、父老乡亲、兄弟单位等,似乎非如此便不能建立和发展自己的人际关系。
血缘关系中,最亲的是母子。中国传统礼教虽然规定父亲的地位最高,但在中国人内心深处,最爱的却是母亲。从&ldo;慈母手中线&rdo;,到&ldo;妈妈的吻&rdo;,最美的赞歌总是献给母亲;从&ldo;孟母择邻&rdo;到&ldo;岳母刺字&rdo;,子女的成长也总是归功于母亲。就连认干亲,中国人也习惯于认&ldo;干妈&rdo;,而不是认&ldo;教父&rdo;。反正&ldo;世上只有妈妈好&rdo;。有没有唱&ldo;世上只有爸爸好&rdo;的呢?没有。歌颂父亲的文学名作好像只有朱自清先生的《背影》,但那父亲却怎么看怎么像母亲。
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,也几乎都是以母亲为中心。比如自己的家叫&ldo;娘家&rdo;,丈夫的家叫&ldo;婆家&rdo;。&ldo;娘家&rdo;不能叫做&ldo;爹家&rdo;,&ldo;婆家&rdo;也不能叫做&ldo;公家&rdo;,反正没当爹的什么事。虽然说&ldo;养不教,父之过;教不严,师之惰&rdo;,但一个人如果当真没家教,也只会被骂作&ldo;没娘养的&rdo;。事实上,中国的母亲也确实了不起。她不但管吃管穿管教育,还管救命。中国的小说中常有这样的情节:一个人,惹了事,闯了祸,小命难保了,要讨饶,便会搬出老娘救驾,道是:&ldo;家中还有七旬老母&rdo;,往往也能奏效,如《水浒传》中李逵之放过李鬼。因为爱母之心,人皆有之,不看爹面看娘面,只好放他一马,以免让那老娘伤心。
比母亲次一点的,则是兄弟。兄弟也很亲。按照中国人的说法,兄弟是手和脚的关系(手足)。尽管说&ldo;亲兄弟明算账&rdo;,祸起萧墙的事也时有发生,兄弟仍被认为是同辈男子问之最亲密者(女性则为姐妹)。所以,一个人要想和别人拉关系套近乎,最便当的办法就是称兄道弟。中国社会各阶层,称谓各不相同,如官场称&ldo;大人&rdo;,商界称&ldo;老板&rdo;,儒林称&ldo;先生&rdo;,江湖称&ldo;大侠&rdo;,唯独&ldo;兄弟&rdo;,放之四海而皆准,什么人都可以用来称呼自己的朋友,或称呼自己,甚至用来称呼各自所属的群体,比如&ldo;兄弟单位&rdo;。就连初通汉语的老外都知道一见面就叫一声:嗨,哥们!
请勿开启浏览器阅读模式,否则将导致章节内容缺失及无法阅读下一章。
相邻推荐:师父们都想我以下犯上 旺夫命 规则怪谈,诡怪都对我穷追不舍 小熊猫的特殊任务技巧 今天夫君杀妻证道了吗 师尊对我爱而不得 少年时gl 终极一班3之选择gl 惟我独尊 秋瑾诗词集 江城谣 有戏 还我惬意的古代生活 [综漫]拯救世界的仁王君 我的人生哲学 你走神儿不如我走神儿 兽王缠身:惹火娇妃霸天下 马克思 夜玫瑰 情仇家国怨